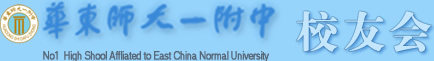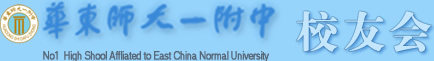我和一附中 ——写在62届高中校友毕业六十周年 
一附中原物理教研组组长 张正大
《我们的芳华》 62届高中学兄们(注:我1957年方进附中工作,而62届高三同学于1956年就进入附中初中部了,故称诸位同学为“学兄”矣!):今年是你们毕业离校六十周年。想当年,我们大家都全身心忙于学和教,虽然相处二、三年,但无暇聚谈交流,故你们并不太了解我。借如今机会,让我说说自己。 一、我的学历 我,无锡人。初中在乡村中学读书,懞懞懂懂,踢踢小皮球。 高中进苏州中学,开了眼界,化学课上看到了玻璃试管,但上数学课、英语课云里雾里,成绩当然班级下游。直到高三时,才跟上了班级步伐。 说心里话,当时我就佩服诸位读书如此优秀,对照自己的中学表现,不禁脸红。 报考大学,第一志愿北京航空学院,第二志愿北京地质学院,体检色盲被删了。第三志愿师范,被华东师大收录了。 在大学里,政治表现、学习成绩,还属上乘。 1957年,大学本科毕业,进我们附中。老教师丁明远曾告诉我,是陆善涛校长到师大去亲自挑选的。1960年,任教研组长。 二、感恩附中 (一)从1957年师大毕业,到1995年退休,共38年,我全服务于附中。 文革前、后,我教授到的,是虹口区最好的学子,这都是因为附中声誉卓著,家长慕名争相把孩子送来报考。同学们又聪敏又好学,授课时看着你们一双双专注、渴望、灵动的眼睛,实在是满满的享受! 日后,果然成长出许多出类拔萃、成就蜚然的杰出人物,中五丁班就出了个中科院院士陈凯先。 陈院士对我多有关照和抬爱,常有些联系,所以他的事迹我略知一二。他先后任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国家生化研究院党委书记、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科技协会会长。感人的是,尽管荣誉满身、重任在肩,但他不忘师恩,热心为母校校刊写稿撰文,在校友会任职服务……。 我作为他的任课教师,也受到垂爱:每年春节都寄我贺岁卡。让我手足无措的是,那年还让陈夫人亲自上门,送我年货。 2006年教师节前夕,他偕同教育电视台二位记者,来我昆山路家中探访(十分平凡,未出报道)。 陈院士曾亲口对我说:当年就是受我物理课的影响,毅然报考了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原子物理)。真让我自傲和享受,作为一个教师,夫复何求! 这就是我们附中的学子!附中的沃土,就是能长出参天大树。 (二)1986年,我被邀参加上海市高考命题。物理命题组共四人,高校教师3人,中学教师1人,交大教授为组长。 我好奇,问怎么会招我参加命题的?考试院领导说:“你们师大附中教学质量高,去年高考物理成绩全市第三”。 1991年,再次邀我参加高考命题。物理命题组仍是高校教师3人,中学教师1人,由复旦大学领衔。 1993年,召我为高考审题组成员。物理审题组三人,高校2人,中学1人,复旦教授为组长。命题组完成命题后,试题需经审题组审阅通过。 我还担任了几届虹口区教师职称中评委成员。 我能荣承这些任务,显然来自于附中声誉卓著。我附中真是一片教育沃土,育学子成英才,炼教师为智者。师生教学相长,共同成长。感恩附中! 三、剖析自己 说说两件事吧。 某日,学校一把手蔡祖康找到我,说要起用我为教导主任。我吃了一惊,深感意外,当场表示自己并不胜任。我的想法是,能担此重任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1、政治上应是党员;2、业务上应粗通语、数、外三门主科教学。而自己並不具备,所以婉拒了。隔了几天,蔡头再次做我工作,我还是推辞,让他失望了。 还有一次,季克勤校长请我到办公室,说学校准备上报推荐我为特级教师!我想,自己学术水平没有“特级”之高度,教课水平没有“特级”之艺术。若戴上“特级”之冠,岂不压力重重?因此表示不敢接受。季校长说,我们做过调查,推举你的人最多。但我还是不敢接受,结果此事作罢。 过了一些日子,再想起此事,有些后悔了。自己太迂腐太狭隘!当时怎么未想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对提高学校、提高物理组的声誉,都是促进的呀!而自己的愚蠢,让学校和自己两失! 检讨以上两事,我自评:没担当! 四、附中特色 勇于探索创新,是附中的特色。 (一) 1951年,在全市中学界,附中开创先例,首先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1952年,华东师大派苏联专家杰普列兹卡娅为附中校长顾问,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建立班集体、设班主任、开班会课、建教研组、写备课笔记、考试5级记分制…。试验成功,成果在全市推广。 (二) 因“科技兴国”需要,1959年春,上海市挑选10所质量高的中学,转制为各种科技学校,我校定为“上海电子学校”。于是,高中物理改为教“电工学”,准备以后再教“电子学”,由出身交大的夏哲公和我各教二个班。这时,我们物理组,成了超越语、数、外主科的教学中心。但不过一学期,上面又改主意了,觉得科技兴国还是得靠大学培养高端人才。于是,“上海电子学校”停办,重新回归师大附中。 (三) 大跃进年代,提出“超英赶美”口号!因此,上海市对普教系统提出两个“适当”,即“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于是,在1960年,上海选了几所重点中学,试行“五年制”,实质是把高中三年缩短为二年。 我校又赶上了潮头,被选上了。首先要解决教材,市委书记杨西光亲自挂帅,组织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和我们一附中,组成教材编写组,同时让上海教育出版社紧跟,密切配合,即编即印。陆善涛校长参加编写化学教材,我参加编写物理教材。日以夜继,奋战半年,部分教材大功告成顺利出版。但新教材並未落实使用,原因很简单,全国高考考纲未变,试点学校不敢使用新教材! 但“五年制”继续实施,高中三年变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方停止。
回想当年教“五年制”班,真是刻骨铭心的岁月!“六年制”高中,已是公认的任务重、压力大。可我校为了改革、探索,却要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高中三年的教学任务,并在高考战场上与他校同场竞技!所以老师们是呕心沥血、精心备课:同学们是发奋努力、自觉学习。而且,我们从不加班加课,还是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结果是,高考中成绩斐然,日后又人才倍出。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感慨万分! (四) 新世纪起我校又提出探索目标:建设“研究型学校、研究型教师、研究型学生”。目标高大上!独树一帜! 2025年,是一附中的百年生日。而今我也已过米寿,正在“奔九”途中。真心期待学校能够“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我在有生之年也能够看到附中的新发展。 
62届校友为纪念毕业六十周年向母校两处校址捐赠的镜子 今年是一附中1962届高中同学毕业六十周年。原准备隆重举办毕业一个甲子年纪念活动,还盛情邀我参加。无奈因疫情无法举办,但是同学们的心意我领了,故以此文略表自己的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