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调查研究面临革命”(载自2015年06月11日 《东方早报》)
2015/7/3
“大数据时代,调查研究面临革命”
来源:2015年06月11日 《东方早报》
■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范伟达 从新书《中国调查史》谈如何提升官方调查和统计的公信力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伟达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范伟达,与《中国调查研究》(网络版)主编范冰合著的《中国调查史》在今年4月出版。这部书凡77万言,纵向上从夏商周直至21世纪,横向上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调查维度,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核心理念贯通全书。
6月5日,早报记者对范伟达进行了专访。访谈中,范伟达特别强调尽管中国有很深厚的调查研究传统,但至今很多领导干部仍然没有认识到调查的重要性,一些所谓的调研总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而对于很多官方统计和调查如何提升公信力的问题,范伟达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希望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和建国后历史的回顾,让人们了解到正确决策几乎都是以深入调查为基础,而忽视调查时往往就会犯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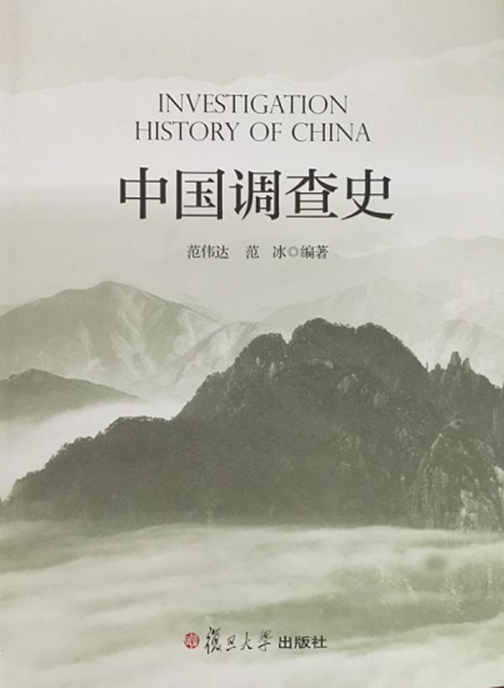
《中国调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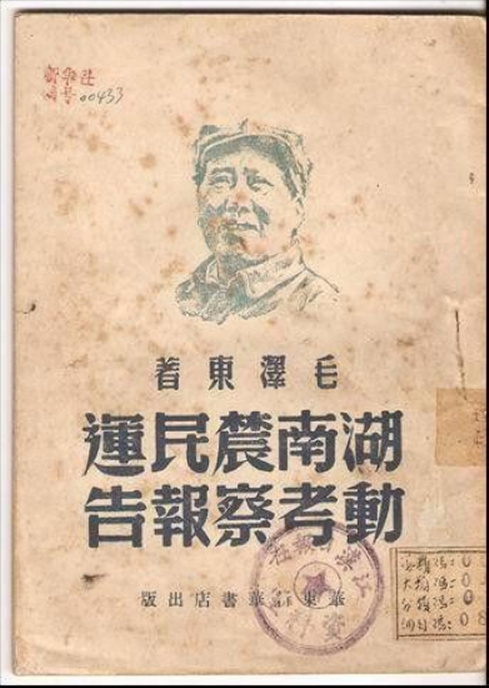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东方早报:为什么“五四”后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运动?
范伟达:“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要救国必须要了解国情,必须要深入民间。特别是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也提到了,“五四”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五四”运动最终还是在工人、农民起来后才取得成效的。
“五四”以后,中国的调查产生了两大传统。一个是学界的、高校的专家教授为主的学术性调查,以陶孟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相当重视调查。从毛泽东在1921年到1922年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开始,一路调查过来,没有这个调查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打不出一个新中国。
东方早报:书中对于当时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给出的核心提示是“以革命为导向”,无论是毛泽东早期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还是之后太行山根据地的农村调查、延安时期的调查,都是如此。如何评价这些调查?
范伟达:调查目的和理论指导对于一项调查的科学与否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调查的目的是改良还是革命,调查的理论是马列理论还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导致最后的调查结论都会有不同。现在很多调查不大注意理论范式的指导,仅从技术层面上进行分析。
另外是从方法上来看,如何从现实世界获取真实的信息。当时学院派用统计、抽样、实地等方法去调查,这些方法都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关注问题的局限,导致采集的信息就可能(与真实信息)不同。而共产党的调查,尽管还没有用到抽样的、概率论的方法,就是田野的、座谈的这种“小米加步枪”的方法,但是能够真正反映民众的意向。
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第二,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调查结论学院派的调查做不出来,因为学院派的视角还是在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真正民众的革命热情和潜力也许就挖掘不到。
东方早报:所以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的决策和道路的选择多半都是基于深入调查、重视调查结果,而很多弯路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不重视调查或忽视调查结果。
范伟达:就是这样。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锦涛同志则讲“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其上升到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相关的高度。
为什么1960年代初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因为之前忽视调查而导致出现了挫折。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邓小平、陈云,包括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都下去调查,回来以后反映下面要搞责任制,包产到户。但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大家调查的结果,说,群众的话要听,但不是什么都听,比如像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一判断失误,马上就批判“单干风”、抓阶级斗争,一直到“文革”。
所以是否重视调查研究,是否把调查研究的结果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不仅是作风和方法的问题,更是关系我们事业得失成败的问题。
东方早报:书中也谈到,时至今日,我们很多的领导干部仍然没有认识到调查的重要性。
范伟达: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邓伟志教授在评论这本书时,特别提到了它的现实意义。他就说我们很多领导干部总喜欢闭门造车,自以为聪明,拍拍脑袋就发号施令。尽管有些人知道点调查,但也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浮而不深的调查。
现在各种调查对数据肆意歪曲,连公信力都没有了。不仅是政府,学界、商业界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但不交代样本的构成,胡乱地访问几个人,就随意地得出结论。
东方早报:我们常说“数据不会说谎”,但不是说真实的数据就会得出正确、准确的结论,何况如何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又是一个问题。
范伟达:前几天我们开会,北大教授刘德寰就说,很多人以为数据就是结论,实际上数据真的不能告诉你任何问题,结论一定是在分析当中。
现在我们都在做数据的生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保证数据生产的真实性很关键。就像我们常说的“谁动了我的奶酪”,放到这里就是谁动了我的数据。为什么现在连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大家都质疑,没有公信力?这就涉及到你的数据究竟是怎么生产的,以及有了数据以后,如何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在“大数据”时代,调查研究面临着一场危机,或者说革命。
东方早报:说到官方调查和统计数据在公信力方面面临的危机,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改进?
范伟达:一个是要让公务员或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真正了解到调查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作秀,为了向上交代,为了政绩,还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调查的出发点不同,调查的结果就完全不同。
第二是要对这些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及其方法的培训。有些人并不是不想调查,或者说并不是没有在做调查,但是不懂什么才是客观的、科学的调查,什么是科学的程序,怎么样得到科学的结论。
第三就是作风和态度问题。因为数据采集、分析,最后结论出来,关键还是人。一个人尽管懂得方法,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照样造假。
另外,今后还要有一些法制和规范建设。现在数据失误造成了负面影响,虚假数据满天飞,没有任何惩罚措施,没有任何责任的追究。当然现在互联网如果有虚假信息已经开始追究责任了,但主要还是对民间。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机构如果出现数据或信息失误的情况,如何来追究责任,要有一些法律法规出来。
东方早报:是不是很多调查放手让民间去做效果会更好呢,比如说民意调查?我在书中看到,您还比较倾向民意调查应该由官方来做。
范伟达:所谓官方或民间,只是指研究的主体性质是怎么样,而并不是说调查的手段和实施人。统计系统、政府部门、媒体的民意调查,从机构的主体来说是官方性质。民间的则可能是调查所、调查公司的。作为趋势来说,特别是民意调查,肯定是要鼓励民营的、民间的公司为主体来进行。
但是中国的现状还是需要有一个过渡,因为我们现在这种NGO类型的民营机构才刚刚开始诞生,发育还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由官方主办的一些调研机构来了解社情民意,也不失为一种方式。
是否重视调查研究,是否把调查研究的结果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不仅是作风和方法的问题,更是关系我们事业得失成败的问题。
(本站按:范伟达教授是我校66届高三毕业生。关于他的著作《中国调查史》的发布会信息可见本站5月16日“新闻资讯”栏目的报道)